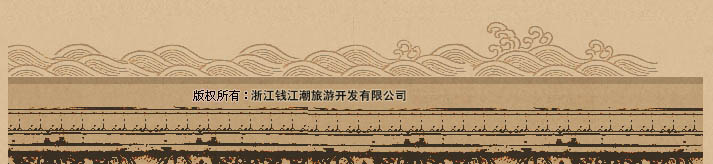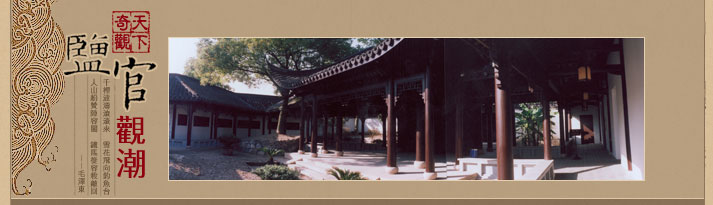
近日,在网上有票选中国十大国学大师的一个活动,王国维以最高票伫立于榜首。听到这个消息时,笔者正在海宁——王国维的家乡,心中一时涌上万千感慨,就在这里缅怀起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学术大师”。
王国维,初名德桢,后改为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人间等。浙江海宁盐官人。
除了以上这些文字是确认无疑的,其实,没有任何传记或介绍文字能把王国维短暂却又传奇的一生写完全了。他就像他家乡那著名的潮一样,不接触他时,如看潮落之江深沉如海;而一旦接触到,恰似观潮起之状浪高势大且多变,让世人除了惊叹就只能崇拜。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许多方面都带着他的痕迹——王国维是学术界绕不开的里程碑,是一个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推进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巨人!
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即公元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海宁州海宁城(今海宁市盐官镇)的双仁巷王家旧宅里。这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并不知道他的家族曾是赫赫有名的安化郡王王府,他也不知道他的远祖王禀是在北宋末年抗击金兵失败时跳汾水自杀的,他更不知道他会给中国学术界带来怒潮滔天一般的震撼。当时,他只是皱紧了眉头“哼哼唧唧”地哭了几声,便展开了他曲折厚重的人生。
王国维4岁的时候,生母凌氏便病故了,他的父亲王乃誉为了维持一家生计终年奔波在外。幼年失恃的王国维和时年9岁的胞姐蕴玉,就全赖年迈的祖姑母和叔祖母抚养。家境贫寒、童年寂寞再加上身体羸弱,使得王国维的性格日益忧郁寡言,但这也养成了他沉静好思的习惯。
7岁启蒙,16岁应乡试中秀才,王国维初露文采,就名噪乡里,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如果没有意外,王国维也许就会像那时的许多秀才一样一生汲汲钻营科举,以求谋个一官半职,重振起安化郡王府的家业。然而,命运的齿轮却把他推到了另一个方向。
成为秀才后没多久,王国维在一次与朋友互相切磋学业时,偶然看到了《汉书》,翻阅后他十分感兴趣,就拿着从小积蓄下来的钱跑到杭州去购买了前四史。这首次的独立置书,也开启了他真正的读书之门。埋头读史的王国维对一直以来学习的八股文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以至于17岁时去杭州府试,不到考试终场就弃笔离开。
笔者常常在想,那时的王国维正值血气方刚,八股文束缚得住凡人却一定是绑不住他那样自由奔腾的灵魂的。果然,第二次府试,王国维又是未终场即离。在他心里蜇伏着的潮头已蠢蠢欲动。
可是,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该做什么?王国维还没有找到他的“杭州湾”。
万幸地是,他出生在一个好地方。
海宁城并不大,可这个小地方却从不落后。海宁人乐于也善于接收吸纳各种新思潮。“西学东渐”之风吹到了海宁,让18岁的王国维看到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
毅然抛弃了科举应试范文的王国维,于22岁踏进了上海的十里洋场。那一年,他题在别人扇子上的一首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被罗振玉看到了。罗认为王国维日后必成“伟器”,便开始资助他的生活与学业。从那时起,王国维才真正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海宁潮起了。
24岁译《势力不灭论》并撰《译例》四款,同时开始我国第一部《浮士德》译著的翻译工作。当年12月,由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
26岁开始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上刊登译作。
28岁起研读叔本华、尼采哲学并译介至中国,成为中国译介西方人本主义美学的第一人。同年撰《红楼梦评论》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力作。
29岁编定《静安文集》,同时编辑《静安诗稿》。
30岁编《人间词甲稿》,并在其《文学小言》中初次倡言审美的“三种境界”之说。
31岁编成《人间词乙稿》。
32岁开始在北京《国粹学报》上连载《人间词话》,首倡意境说。
36岁时动笔撰《宋元戏曲考》,37岁书成并更名为《宋元戏曲史》,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整理古典戏曲的著作。
38岁完成研究西北古地理的著作《屯戍丛残考释》,罗振玉为之撰写考释并付诸石印,书名署作《流沙坠简》。王国维作《流沙坠简序》。岁末又为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作序和后序。由此成为国际新兴科学甲骨学、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
40岁开始治学新方法,撰写了《毛公鼎考释》、《魏石经考》等著作。
41岁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并写成《殷周制度论》,被世界学术界公推为甲骨文考释及商周史研究之最伟大的著作。这一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几次派人来聘请王国维任教,都被他谢辞了。
43岁时王国维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向西北地理。也是这一年,他被溥仪召入宫担任了“南书房行走”之职。有清一代,除了大学者朱彝尊就只有王国维以布衣之身入值南书房,足可见此时王国维的学术地位。
46岁时王国维经不住北大几番诚邀,终于同意担任该校国学门的通讯导师。
47岁校《水经注》,出版了《观堂集林》。
48岁时王国维已为学术重镇,胡适推荐其担任清华研究院院长,校长曹云祥亲往聘请,却被他婉言辞谢了,还于当年12月辞去了北大职务。但是清华园并没有放弃,49岁的王国维最终答应了清华的教授聘任,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学术也日益精深。
王国维少年才气骏发,中年蓬勃外铄,晚年更是大器宏深,而贯穿其一生的是对学术如涌潮般猛烈热忱的追求与献身精神。他视学术即为自我之性命,尤视学术为国家与民族命脉之一绪。他用别具眼光的透视角度,自觉地从世界文化背景来观察中华学术在近代、在传统轨道上发生的震颤与位移,又从而自任学术使命,导引辟径,树起了中天之帜。
王国维识见卓越,他创“二重证据法”,拓学术区宇,历练三级境界;他考证义据精深,方法系统缜密;他创新说却又未废旧闻,尊前贤又不为虏属;他的学术论文雕龙而典雅,绵密却练达,他蕴蓄深广,采择精博,是真正与世界学术对话、接轨的国学大师,世人对其“高山仰止”。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国维一生虽然涉猎广博,却难得的杂而精。他在他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学术著作六十余种,其中四十三种由商务印书馆编成《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出版,即有一百零四卷。
陈寅恪说:王国维之所以能在学术上作出如此卓越独特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能热情地投入新潮流”。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是王国维自己在引领新潮流。
始终立于潮头的王国维在1927年6月2日突然纵身一跃,永远地沉入了昆明湖中,把中国“可以想望的一座九仞高台击了个粉碎”。噩耗传来,举世震惊,当时各大报刊均以头版头条刊登了他的死讯。梁启超闻讯抱病由天津赶至北京,亲自操办他的后事,清华园亦破例为其树碑纪念。然而正如日中天的学术巨擘骤然辞世,只留下一个如海宁潮般复杂神秘的谜,还是让后世无限地惋惜唏嘘……
谁也看不透王国维,谁也追赶不上他的步伐,谁也无法抗拒他的学术魅力。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他这里所称的“境界”是指修养的不同阶段,而也许今天的我们也能借其言评其人:王国维,潮的最高境界!
|